佛教现代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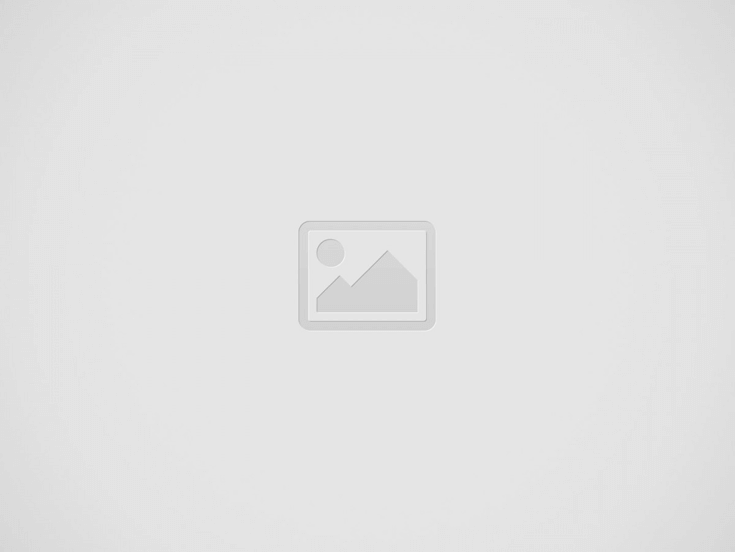

佛教现代主义(也被称为现代佛教和新佛教)是基于佛教现代重新解读的新运动。 大卫麦克马汉指出,佛教中的现代主义与其他宗教中的现代主义相似。 影响的来源多种多样,是佛教社区和教师与“西方一神论,理性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以及浪漫表达主义”等新文化和方法的融合。 一神论的影响一直是佛教神灵的内化,使其在现代西方被接受,而科学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影响了对当前生活,经验辩护,理性,心理和健康利益的重视。
新佛教运动的教义和实践与历史上主流的Theravada,Mahayana和Vajrayana佛教传统不同。 佛教现代主义是西方东方主义者和具有改革头脑的亚洲佛教徒的共同创造,是对佛教概念的重新表述,强调了传统的佛教教义,宇宙学,仪式,修道主义,文职等级和图标崇拜。 这个词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对亚洲宗教的研究中盛行,在路易斯·德拉瓦利普桑1910年的文章中找到。
佛教改革运动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斯里兰卡的佛法拉(Dharmapala),他们从根本上批评了传统佛教,重新评估了平信徒的角色,并将冥想作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佛陀的教义建立在理性,理性主义,无神论,科学,生活哲学而不是宗教的基础上。 强大的政治化和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是这些运动的特点。
其结果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现代主义(也称新佛教)作为16世纪以来欧洲征服和基督教使团施加压力的佛教原始文化更新运动。 为了回应这种异化,他们开始寻找自己的民族认同,并首先回顾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这被认为是反对西方化进程的壁垒。 与殖民地位有关的本土文化的耻辱和贬值以及殖民统治者的歧视最终导致了实际上世界偏远的佛教的政治化。 进步的西方思想,如民主和社会主义,
例如佛教现代主义的内斯特和僧伽罗爱国主义者Anagarika Dharmapala等佛教现代主义者声称民主是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产物。 维拉亚瓦尔德纳在维尔亚瓦尔德的社区看到了一个早期的共产主义形式的社区,并写道:“佛陀所建立的早期僧团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规则和实践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是一个无阶级的社区[…]他们没有个人财产;整个庄园属于社区。“(DC Vijayavardhana,1955年TempleColombo的起义,第595页)。 维杰亚瓦尔德纳强调,理想的佛教生活方式和真正的共产主义在经济层面上是完全相容的。 这位作者在写道:“当然,佛教与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教义的哲学观念方面存在根本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它基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教会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同上)这与佛教的精神相矛盾,所有的物质事物最终都是幻想。 诚然,Urbuddhism的修道院财产社区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是由同一种精神诞生的,
与此同时,通过对过去的理想化,政治要求使佛教恢复到旧的特权地位,并恢复到国教,这是佛教在锡兰和缅甸历史悠久的君主政体时代一直拥有的地位。 这就是“政治僧侣”的时代,他们无视维纳亚的规则,以游说的方式干预政治,为在国家和社会中恢复佛教而奋斗。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新佛教运动对东南亚部分佛教国家的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助于民主制度的稳定:在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的情况下,重要的是他们的合法性可以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这有助于他们的接受。 例如,佛教秩序的民主结构(僧伽)被看作是要转移到国家和社会的模式(例如,平等原则和多数投票原则):在僧伽中,所有僧侣原则上是一样的,修道院的修道院是由僧侣们的大会选定的)。 通过这种方式,民主自治原则可以作为佛教传统的一部分。 这应该转移到国家和社会(例如平等原则和多数投票原则):在僧伽中,所有的僧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而修道院的方丈则由僧侣的议会选出)。 通过这种方式,民主自治的原则可以被认为是佛教传统的一部分。 这应该转移到国家和社会(例如平等原则和多数投票原则):在僧伽中,所有的僧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而修道院的方丈则由僧侣的议会选出)。 通过这种方式,民主自治的原则可以被认为是佛教传统的一部分。
新佛教,特别是斯里兰卡和缅甸的Theravada佛教国家,激励了政治自由运动,并促进了民族独立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 从西方借用的自由和平等思想被用作反对英国殖民国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
佛教现代主义运动和传统的例子包括人文佛教,世俗佛教,从事佛教,纳瓦亚纳,由日本发起的日莲佛教新组织,如创价学会,新卡达姆传统和西藏佛教大师的传教活动引领法国迅速发展的佛教运动),内观运动,Triratna佛教共同体,达摩鼓山,佛光山,佛教,慈济和瞻博基金会。
概观
佛教现代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殖民时代出现,作为西方东方学家和改革思想的佛教徒的共同创造。 它挪用了西方哲学的元素,心理洞见以及越来越感觉为世俗和适当的主题。 它不再强调或否认仪式元素,宇宙学,神,图标,重生,业力,修道,神职等级和其他佛教概念。 相反,现代主义的佛教强调内心的探索,对当前生活的满足以及宇宙相互依存等主题。 佛教现代主义的一些倡导者声称,他们的新诠释是佛陀的原创教义,并指出Theravada,Mahayana和Vajrayana佛教中发现的核心教义和传统习俗是佛陀死后插入并引入的外来增生物。 根据麦克马汉的说法,今天在西方发现的佛教形式深受这种现代主义的影响。
佛教现代主义传统是重构和重新强调理性,冥想,与现代科学关于身心的兼容性。 在现代主义的演讲中,Theravada,Mahayana和Vajrayana佛教徒的做法是“非传统的”,因为他们经常以阻碍他们历史建筑的方式呈现。 相反,佛教现代主义者经常对他们的传统进行本质化描述,其中关键原则被重新制定为普遍的术语,而现代主义的做法与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的亚洲佛教社区显着不同。
历史
西方最早的佛教记载是19世纪的欧洲旅行者和基督教传教士,他们指出科尔曼将其描述为另一个“带有奇怪的神灵和异国仪式的异教信仰”,他们担心的不是理解宗教而是揭穿它。 到19世纪中叶,欧洲学者给出了一幅新的图景,但是在西方理解的概念中又一次。 他们将佛教描述为一种“拒绝生命的信仰”,拒绝所有的基督教思想,如“上帝,人,生命,永恒”; 这是一个异教的亚洲宗教,教导涅磐,后来解释为“歼灭个人”。 1879年,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的着作“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以佛陀生活的形式对佛教进行了更为富有同情心的描述,强调了佛陀与基督之间的相似之处。 欧洲的社会政治发展,诸如查尔斯达尔文等科学理论的兴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引起了对佛教和其他东方宗教的兴趣,但它在西方和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系统与流行的文化前提和现代主义。 Heinz Bechert于1966年首次全面研究了Theravada传统中的佛教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 贝舍特在斯里兰卡等后殖民社会中将佛教现代主义视为“现代佛教复兴主义”。 他确定了佛教现代主义的几个特点:对佛教早期教义的新解释,对佛教的神秘化和重新解释为“科学宗教”,社会哲学或“乐观主义”,强调平等和民主,“激进主义”和社会参与,佛教民族主义和禅修实践的复兴。
日本:新佛教
在日本佛教和西方交往中,新佛教和现代主义一词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出版物中。 例如,Andre Bellesort在1901年使用这个词,而Louis de la Valllee Poussin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它。 根据詹姆斯科尔曼的说法,在西方观众面前的现代主义佛教的第一位主持人是1893年在世界宗教世界大会上的Anagarika Dharmapala和Soyen Shaku。 Shaku的学生DT铃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英文流利,他向西方人介绍了禅宗佛教。
“新佛教”与日本民族主义
Martin Verhoeven和Robert Sharf等学者以及日本禅僧G. Victor Sogen Hori认为,由新佛教思想家如Imakita Kosen和Soyen Shaku传播的日本禅宗品种并不是日本人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时代禅宗,现在也不是典型的日本禅宗。 虽然明治维新被大大改变了,但日本禅宗仍然是一种修道传统。 日本的禅宗传统除了新佛教的风格之外,还需要很多时间和纪律,因为僧侣很难找到这种僧侣。 在进入修道院之前,禅宗僧侣经常被要求花费数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背诵经文并阅读评论,然后才进入修道院接受三with的罗恩练习。 铃木自己能够成为外行人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是新佛教的结果。
在1868年日本进入国际社会并开始工业化并以惊人速度现代化的明治时期开始时,佛教在日本被简略地迫害为“腐败,颓废,反社会,寄生和迷信信条,不利于日本对科学技术进步的需求。“ 日本政府致力于消除被视为外国的传统,而不能培养对国家意识形态凝聚力至关重要的情感。 除此之外,工业化也对佛教徒造成了伤害,导致数百年来资助寺院的教区系统崩溃。 为了应对这种看似棘手的动荡局面,一群现代佛教领袖出现为佛教事业辩论。 这些领导人同意政府迫害佛教,指出佛教机构确实已经腐败,需要振兴。
这种日本运动被称为shin bukkyo,或“新佛教”。 领导人本身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接触过大量的西方知识文学。 西方作为日本禅宗呈现的东西与启蒙运动对“迷信”,制度或仪式为基础的宗教的批评是如此相称的事实是由于这个事实,因为这样的理想直接导致了这种新传统的产生。 这种重新构思工作的根源在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仁伯努夫的着作中,他表达了他对“婆罗门,佛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喜爱和对马克斯穆勒的“耶稣会士”的不喜欢。 Imakita Kosen将成为DT Suzuki的禅宗老师直到1892年去世,他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在对宗教改革对精英制度主义的批判作出很大反应时,他开设了Engageji修道院,以培养像铃木这样的学生前所未有的禅修。
像Kosen和他的继任者Soyen Shaku一样,新佛教的倡导者不仅将佛教这一运动视为防御佛教反对政府迫害的手段,而且还将它视为一种将国家带入现代世界作为一种竞争性文化力量的方式。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科森本人甚至被日本政府聘为“国家传教士”。 日本民族主义的事业和日本作为国际舞台上优秀文化实体的描绘,是禅宗传教运动的核心。 尽管这个版本的禅宗是日本最近的一项发明,但禅宗将被吹捧为日本人必不可少的日本宗教,完全体现为武士道或武士精神,这是日本人充分表达的意思,基于西方的哲学理想。
1892年科森去世后,禅宗的禅师Soyen Shaku声称“宗教是西方人民知道自己不如东方民族的唯一力量……让我们把大车(大乘佛教)西方思想……明年在芝加哥(指1893年的世界宗教议会)适合时间将到来。“根据马丁·韦霍文的说法,”西方的精神危机暴露了它的阿基里斯的脚后跟被征服。 尽管西方列强在经济和技术上受到挫折,日本却有机会通过宗教来重申其文化优势感。“
DT铃木
出于多种原因,一些学者已经确定了DT Suzuki–其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西方流行,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 作为“佛教现代主义者”。 铃木对禅宗的描述可以归类为佛教现代主义,因为它具有所有这些特征。 他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哲学和文学有着深入的了解,这让他在向西方观众争论他的案子方面特别成功并具有说服力。 正如铃木所说,禅宗佛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宗教,它强调直接经验使其特别可与威廉詹姆斯等学者强调的神秘主义形式相媲美,成为所有宗教情感的源泉。 正如麦克马汉所解释的那样,“在讨论人性和自然时,铃木将禅宗文献从其社会,仪式和伦理的背景中提炼出来,并根据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英国浪漫主义和美国超验主义的形而上学语言进行重构。 “ 凭借这些传统,铃木推出了一个被敌对评论家描述为传统和本质化的禅版:
禅是所有哲学和宗教的终极事实。 每一个智力努力都必须达到高潮,或者说,如果要实现任何实际成果,就必须从这个努力开始。 如果它必须在我们的积极生活中有效地证明并且活泼可行,那么每一个宗教信仰都必须从中产生。 所以禅并不一定是佛教思想和生活的源泉, 它在基督教,穆罕默德主义,道教,甚至实证主义的儒家思想中都非常活跃。 是什么让所有这些宗教和哲学变得重要和鼓舞人心,保持其有用性和效率,是因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禅宗元素。
像Robert Sharf这样的学者认为,这些言论也背叛了许多早期佛教现代主义者所共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他们将禅意描绘成代表日本人民的本质,比其他所有宗教都优越。
印度:Navayana
20世纪50年代,印度达利特领导人BR Ambedkar成立了一个新佛教运动。 Ambedkar于1956年10月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拒绝Theravada和Mahayana车辆以及印度教。 然后,他采纳了纳亚亚那佛教,并将五十万至六十万达利特转化为他的新佛教运动。 所有的宗教现代主义元素,国家克里斯托弗女王和莎莉金,都可以在安伯德卡佛教中找到,他的佛陀和他的法师放弃了传统的戒律和习俗,然后将科学,行动主义和社会改革作为一种宗教佛教的形式。 安格德卡的佛教表述与西方现代主义不同,斯卡里亚将他将现代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综合为古代佛陀的思想结构。
根据Ambedkar的说法,一些传统佛教传统的核心信仰和教义,如四谛和Anatta有缺陷和悲观,可能会被后来错误的佛教僧侣插入佛经。 在Ambedkar看来,这些不应被视为佛陀的教义。 Ambedkar将其他基本概念如Karma和Rebirth视为迷信。
纳瓦亚纳放弃了戒律后的和尚,诸如业力,来世重生,轮回,冥想,涅and以及佛教传统中被认为是基础性的四种贵族真理等观念。 Ambedkar的新佛教拒绝了这些观点,并根据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重新解释了佛教的宗教信仰。
Ambedkar称他的佛教版本为Navayana或Neo-Buddhism。 他的书“佛陀与他的法”是纳瓦亚纳追随者的圣书。 根据Junghare的观点,对于Navyana的追随者,Ambedkar已经成为了一位神灵,并且在实践中受到崇拜。
西方:归化佛教
其他形式的新佛教在亚洲以外发现,特别是在欧洲国家。 根据佛教宗教研究教授伯纳德福尔的说法,西方发现的新佛教是一种现代主义的重述,是一种对个人焦虑和现代世界没有扎根的精神反应形式古老的想法,但“一种非人格无味或无味的灵性”。 这是一种重新适应,一种佛教“点菜”,它理解需要,然后重新填补西方的空白,而不是反映佛教的古代经典和二次文学。
一些西方的佛教解释者为这些运动中的少数提出了“归化佛教”一词。 它没有重生,业障,涅,,存在的境界和其他佛教概念,并以现代主义的语言重新阐述和重申了四谛。[注1]这种“瘪世俗佛教”强调同情,无常,因果关系,无私的人,没有菩萨,没有必然,没有重生,以及自然主义者接近自己和他人的福祉。 以自我发展为中心的内观及其变体的冥想和精神实践仍然是西方新佛教运动的一部分。 根据詹姆斯科尔曼的说法,西方大多数内观学生的重点“主要是冥想练习和一种朴实的心理智慧。”[注2]
对于许多西方佛教徒来说,四谛真理教学中的重生教义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网络1] [注3]根据羔羊的说法,“现代西方佛教的某些形式认为它纯粹是神话的,因此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 西方人发现“业障和复兴的想法令人费解”,达米安基恩 – 佛教伦理学教授。 虽然大多数佛教徒在亚洲确实接受这些传统教义并寻求更好的重生,但可能并不需要相信某些核心佛教教义是佛教徒。[注4]重生,业力,存在领域和循环宇宙教义支撑佛教四大圣谛。 有可能重新解释佛教教义,如四圣谛,Keown州,因为最终目标和痛苦问题的答案是必杀技而不是重生。
据Konik介绍,
由于早期印度佛教和当代西方佛教的根本问题不尽相同,因此将第一个方法开发的解决方案应用于第二个方案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简单地结束重生并不一定会使西方佛教徒成为最终的答案,因为它肯定是早期的印度佛教徒。
传统的佛教学者不同意这些现代主义的西方诠释。 例如,比丘菩提认为,尽管存在“现代主义的佛教解释者”似乎存在的问题,重生是佛经教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 [注释5]另一个例子,拒绝“现代论证”,“人们仍然可以获得所有的实践结果,而不必接受重生的可能性。” 他说:“重生一直是佛教传统的中心教学。”[网页2] [注6] [注7]
根据欧文·弗拉纳根的说法,达赖喇嘛声称“佛教徒相信重生”,而且这种信念在他的追随者中很普遍。 然而,达赖喇嘛的信仰补充了弗拉纳根,比普通佛教徒更加复杂,因为它与轮回不同,佛教中的复生被认为是在没有“atman,self,soul”的假设下发生,而是通过“意识沿着修行者的路线构思“。[注8]重生学说在藏传佛教和许多佛教教派中被认为是强制性的。 根据梅尔福德斯皮罗的说法,重新诠释佛教的废除重生破坏了四谛,因为它没有解决佛教关于“为什么活着?”的存在主义问题,为什么不自杀,通过结束加速当前生活的结束生活”。 在传统的佛教中,重生延续了dukkha,停止dukkha的途径不是自杀,而是四谛的第四个现实。
据Christopher Gowans说,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佛教徒来说,今天以及过去,他们的基本道德取向都受到对业力和重生信念的支配”。 佛教的道德取决于这一生或未来重生的福祉的希望,而涅((启蒙)是未来一生的项目。 否认业力和重生破坏了他们的历史,道德取向和宗教基础。 然而,Gowans补充道,许多西方粉丝和对探索佛教感兴趣的人都持怀疑态度,并反对对“四圣谛”的基本业力和重生的信仰。[注9]
据Gowans称,“归化佛教”是对传统佛教思想和实践的彻底修改,它打击了东方,东南亚和南亚传统佛教徒对人类生活现实希望,需求和合理化的背后结构。
其他新佛教
据比较宗教教授Burkhard Scherer介绍,这些新颖的解释是一种新的,独立的佛教派别宗族和香巴拉国际“必须被描述为新佛教(科尔曼)或更好的是新佛教”。
根据Burkhard Scherer的说法,在中欧和东欧,由Hannah和Ole Nydahl开始的快速发展的钻石之道佛教是一个新的orthoprax佛教运动.Nydahl及其600个佛法中心的魅力领导使其成为最大的转换运动在东欧,但其对藏传佛教和密宗冥想技术的解释却受到传统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批评。
其他人则用“新佛教”来形容或发表社会参与佛教的宣言。 例如,大卫布拉泽尔在2001年发表了他的“新佛教宣言”,其中他呼吁将焦点从修道主义和传统佛教教义彻底转移到与世俗世界接轨的全新的解释。 布拉泽尔认为,诸如Theravada和Mahayana等传统佛教传统一直是“制服人口而不是解放人民的国家政策的工具”,并成为“个人得救而不是世界疾病根源”的道路。
洛佩兹的“现代佛教”概念
Donald S. Lopez Jr.用“现代佛教”一词来形容整个佛教现代主义传统,他建议“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跨国佛教教派”,“这是一种跨越文化和国界的国际佛教,创造。 ……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分子网络,最常用英文写作“。 这个“教派”既不是地理学也不是传统学校,而是不同地方各种佛教学校的现代方面。 此外,它有自己的世界主义血统和规范的“经文”,主要是流行和半学术作家的作品 – 来自现代佛教形成时代的人物,包括Soyen Shaku,Dwight Goddard,DT Suzuki和Alexandra David-Neel,以及最近的数字,如Shunryu Suzuki,Sangharakshita,Alan Watts,Thich Nhat Hanh,ChögyamTrungpa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