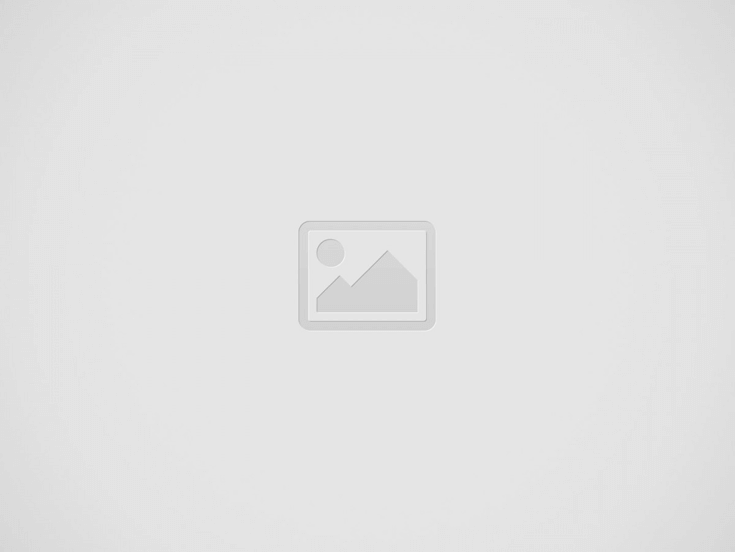

威尼斯双年展2015年南非馆的主题是“明天还剩下什么”,取材于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国际艺术展,《世界的未来》,《玫瑰与提尔》展示了一系列由艺术家们投入的深厚投资在权力,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局部迭代中。策展人不仅希望代表南非最近的重要作品,而且还希望就当代时刻与过去叙事之间的关系展开一场复杂而充满活力的辩论。
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寻求了将新作品插入一系列历史性时刻的方法,而又不以任何方式使这些时刻变得明确或暗示对历史的残酷反对或认同。相反,他们将过去视为(并试图代表)南非破裂和多声的现在中的冲积流,一连串的梦想,愿望和记忆经常以有用和破坏性的方式浮出水面。
展览中的当代作品构成了一系列反作用。有些人对历史不感兴趣,而把重点放在了目前的破裂上。有些人将自己融入反省的解放和民族身份叙事中,以期使这些叙事的确定性不安。有些人通过代表个人生活中充满烦恼的特殊性和奇异性,来质疑民主和国家建设的伟大神话。有些是关于迷失,逃避或希望的微妙冥想;其他人则强烈反对该规范。
展览采取了两个近期的历史出发点,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最近的仇外心理袭击,策展人的目的是“动摇民主,ubuntu和民族主义的无用神话”。
节目中包括Warrick Sony对Marikana大屠杀的看法。 Haroon Gunn-Salie的“ Soft Vengeance”(软复仇)是Adderley街上Jan van Riebeeck雕像手臂和手的红色塑形,是#RhodesMustFall运动的重点。 (我想起了一位评论员的建议,即南非馆仅包含开普敦大学退役的罗德雕像。)
杰拉尔德·马科纳(Gerald Machona)的《来自遥远的人们》,使用外星人和太空探索者的象征来应对作为津巴布韦人来到南非的困难,以及莫哈·莫迪萨肯(Mohau Modisakeng)的影片《 Inzilo》,在该录像带中,艺术家参与了祖鲁人的早晨仪式,两者都将艺术家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美学交集中的身体。
没有现场工作或表演,没有干预,甚至没有任何实际的安装工作,似乎也没有尝试任何其他策展策略。
策展人
杰里米·罗斯(Jeremy Rose)于1996年与菲尔·马莎巴恩(Phil Mashabane)共同成立了马莎巴恩·罗斯合伙公司(MRA)。罗斯曾担任多个博物馆,遗产和公共艺术项目的首席建筑师,包括曼德拉捕获遗址博物馆,曼德拉牢房雕塑,自由公园博物馆,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的囚徒,巴黎,古德曼画廊海角,曼德拉故居访客中心,赫克特·皮特森纪念馆和博物馆,种族隔离博物馆,莉莉叶解放中心,里沃尼亚,起源中心维特斯大学,曼德拉捕获遗址公共雕塑(与艺术家马可·西安范内利一起),搬入舞蹈,纽敦,奥普拉·温弗瑞领导力女子学院和约翰内斯堡大学艺术中心。
MRA是第26届索菲亚·格雷(Sophia Gray)纪念奖获得者,被列入自由公园博物馆(Freedom Park Museum)的世界建筑节(巴塞罗那)文化类别入围名单,并获得了自由公园纪念馆(Freedom Park Memorial)的世界建筑节(巴塞罗那)的表彰。 MRA赢得了Liliesleaf解放中心的南非建筑师学会奖,自由公园的比勒陀利亚建筑师学会奖,自由公园奖,赫克特·皮特森纪念馆和博物馆的公共空间立方奖,南非建筑师学会的南非奖。种族隔离博物馆卓越奖和种族隔离博物馆大奖大奖。
克里斯托弗·蒂尔(Christopher Till)的职业生涯始于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Zimbabwe)的馆长,此后于1983年至1991年担任约翰内斯堡美术馆(Johannesburg Art Gallery)的总监。作为约翰内斯堡市文化总监,他建立了该市的第一个文化办公室,并协助建立了约翰内斯堡市。文化艺术政策。他负责建立1985年的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和1992年的约翰内斯堡国际艺术节,并负责重建市政剧院(现为约堡剧院)。他是新镇文化区重建中的重要角色。他是国际博物馆理事会美术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也是开普敦三年展组织委员会的主席。他是约翰内斯堡种族隔离博物馆和开普敦非洲黄金博物馆的馆长。目前,蒂尔(Till)指导比勒陀利亚大学新的Javett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规划和开发。
展览
剩下的就只有明天……缓慢暴力的过去永远不会过去……在撰写本引言时,一张照片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引爆了。在《南非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头版上,莫桑比克一名名叫伊曼纽尔·西特霍(Emmanuel Sithole)的男子被示威,当时人们在看望时被刺伤。我们这些人-不仅在南非,而且在全世界-都很幸运,能够在我们的家中舒适地滑动报纸,放下咖啡杯,然后再次看这个可怕的形象。
这张照片及其所发生的事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致命且无用的,代表了该展览的核心和基本思想,即过去又回到了我们的身旁,事实上,过去绝不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当代时机并规划我们的未来,使其比现在更公平,公正和人道,那么我们就必须再次努力应对我们的历史。
因此,我们展览的标题“明天还剩下什么”既不是对这一历史喜忧参半的接受,也不是空想。相反,它传达了一种渴望,要权衡当前与之前的事物,并提出替代的存在方式和创造世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们从Okwui Enwezor的标题中获得了提示,该标题是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艺术展“世界的未来”,并根据我们的了解对其做出特殊的解释。我们最了解的是(最直接影响我们生活的)是通过一系列暴力和爆炸事件在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些局部性的动荡被嵌入在权力和资本的全球矩阵中,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开始了解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的确,如果我们将自己的困境和成就读为一个狭alone的,特质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和表现,而我们一个人对此负有责任,我们就会下沉。
权力和资本是多价的,并且以各种形式存在。它们使我们与一系列的关系紧密相连,这些关系不仅从过去(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中产生)而来,而且与历史上产生国家和国家概念的宏大叙事有所不同。权力和资本利用民族国家,但他们不相信民族国家。他们只相信所有权和利润,并利用国家的陷阱将这些特权扩大到少数人。
另一方面,国家相信自己,并将自己的民族神话延续为一个连贯的实体,由历史在逻辑上加以解释,公民必须宣告效忠并排斥其他人。这是一个未经审查的方面,不是目前在南非爆发的仇外心理,而是围绕该现象的分析性论述。
因此,尽管做出了激烈而愤怒的反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暴力行为的强烈谴责,以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而有尊严,但评估中仍然存在一个盲点。仇外心理归因于失业和贫困,人们抱怨缺乏向社区提供基本服务的问题,但是在讨论中反复出现的批评是对政府未能监管越来越多的边界漏洞的批评。
对警察的这一迫切需要深信不疑的信念,即有些人“自然”在内部,而有些人在“外部”。当然,体面,守法的人谴责外面的人的迫害,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可以撤消(或质疑)什么被认为是他们根本缺乏归属感。
在这里展示其作品的艺术家冒险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对关于谁在里面和谁在外面的深层次假设提出质疑。他们有一种必须要审视的关于归属的叙述。无一例外,尽管毫无疑问,他们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容易受到暴力威胁,但他们也意识到,在暴力威胁之下,是阴险,“较慢”的暴力形式,从内而外吞噬着我们。
然而,在策划明天剩下的东西时,我们并不想仅仅展示能为我们的社会锦上添花的作品,或者提供一系列的错误和不公正现象,以使国际观众感受到当地的时代精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个人和共同从事的工作使我们对错误清单或成就清单深表怀疑。这样的事情只会给我们做某件事的幻想。我们都在公共部门,博物馆设计和策展,建筑实践等领域工作,这有时使我们不得不居住在过去。这样做使我们对怀旧和对历史的神话化,博物馆学方法的危险保持警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放弃过去是重要参考的想法,这是知道该怎么做的关键,即使作为人类,我们似乎无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但是,我们不是历史学家。相反,我们从视觉和身体角度思考世界。
在视觉上,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思考事物的外观;在身体上,我们大部分工作都在考虑人类如何穿越空间,建筑环境和景观并与之互动。因此,为了从放置在单个封闭空间中的一组单个艺术品的潜在刺耳声中创造出某种东西,我们组织展览的目的不是围绕一个主题,而是围绕一个短暂的主题,以一个小的,黑暗的信号为标志,是展览一端的房间单元,其他作品或多或少围绕着该房间。
这个房间直接参考了1963–4年的Rivonia叛国审判。紧邻它的录像作品将审判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联系起来,该委员会于三十二年后开始,旨在恢复正义。此处将这两个时刻无可否认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是要暗示一个人实现了另一个。当然,邀请观看者重温这些过去的事件,但是其他作品的出现则不允许怀旧,也没有成就感。
这两个装置的材料分别来自种族隔离博物馆,并由种族隔离博物馆委托运行。种族隔离博物馆是南非的一个机构,与过去(糟糕的过去)的关系是无可争议且必要的。然而,在展览的背景下,这些博物馆的文物现在不可避免地被美学化了。这是一个故意的操作,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准确地通过美学的眼光看过去。并不是为了疯狂地美化它,而是因为我们赋予了自己对它适用与在博物馆中可能适用的不同规则的自由。
因此,我们已经将其历史背景的两个部分(审判和真相委员会)与他们的原始背景和博物馆的家分开,以便通过不同于通常向我们开放的途径来重新审视历史。我们聘请了一群艺术家来帮助我们制定这一程序(这样做是在他们的作品上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暴力,使集体展览无法逃脱)。
尤其是,我们曾想过,循环录制一个男人说话时无声无息的声音,这种声音安静而热情地捍卫了推翻白人统治的斗争。不仅声音的质感,而且捕捉节奏的不完善技术的质感,都将使我们听到以前从未听过或很长时间未曾听过的声音。我们曾想过,在黑暗的空间里纯粹重复发声不仅会打动听到声音的人,而且会动摇民主,ubuntu和民族主义的无用神话。
威尼斯双年展2015
2015年艺术双年展结束了三部曲,始于2011年由比斯·库里格(Bice Curiger)策展的展览《照明》,以及马西米利亚诺·朱尼百科全书宫(2013年)。 La Biennale凭借《世界未来》,继续研究有用的参考资料,以对当代艺术做出美学判断,这是先锋艺术和“非艺术”艺术终结之后的“关键”问题。
通过由Okwui Enwezor策划的展览,双年展La Laennare再次观察艺术与人类,社会和政治现实发展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外在力量和现象来施加压力:外在紧张的方式世界征求艺术家的敏感性,活力和表现力,他们的欲望,灵魂的动作(他们内心的歌声)。
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成立于1895年。保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自2008年起担任总统,在1998年至2001年之前担任总统。双年展(La Biennale)站在研究和促进当代新艺术潮流的最前沿,组织展览,节日和研究在所有特定领域:艺术(1895),建筑(1980),电影(1932),舞蹈(1999),音乐(1930)和戏剧(1934)。它的活动记录在最近已完全翻新的当代艺术历史档案馆(ASAC)中。
威尼托地区及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学校参加了教育活动和引导性访问,从而加强了与当地社区的关系。这将创造力传播给新一代(2014年有3,000名教师和30,000名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得到了威尼斯商会的支持。还建立了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以进行特别的参观和展览。从2012年到2014年的三年中,有227所大学(79所意大利大学和148所国际大学)加入了双年展会议项目。
在各个领域,与知名老师直接接触的年轻一代艺术家都有更多的研究和制作机会;通过国际项目双年展学院,这一点变得更加系统和连续,现在在舞蹈,戏剧,音乐和电影领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