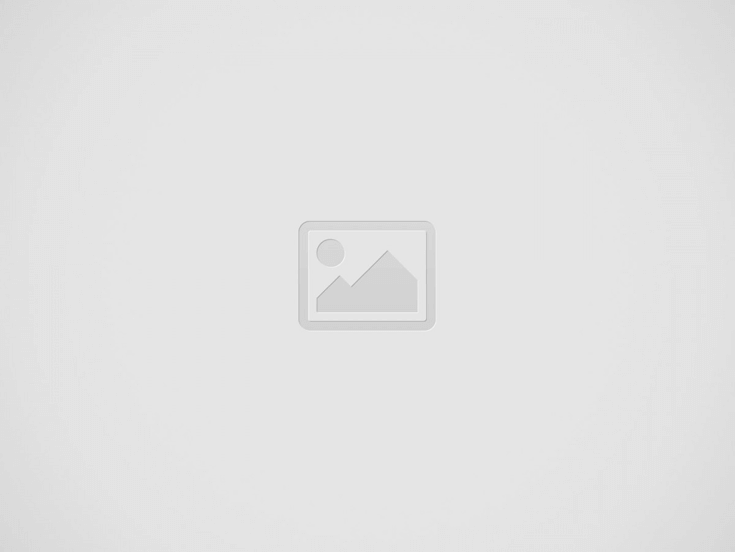

展览首先是一个空间,书籍或档案馆也是。与展览,书籍和档案馆一样,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空间(至少可以说是Georges Perec),包括那些否认或超越这些视觉和知识手段的空间。哈里斯·埃帕米妮达(Haris Epaminonda)的分散项目(尼科西亚,塞浦路斯,1980年)主要是空间性的:对一个地方的命名和介入方式进行了研究。因此,显示的内容与显示方式一样重要。因此,道具元素具有决定性,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必须了解空间,档案,书籍和展览,因此,
Haris Epaminonda的个人项目就像手稿一样,保留了以前的痕迹,而其作品已被删除或修改以产生另一个新项目。最后,他的方法是在已经写过的东西上写东西,在已经被干预的东西上干预,修改已经被修改的东西,展示已经展示的东西。
他的作品(在安达卢西亚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基于变化的,经常会得到微小的变化的支持,这些变化会在意味深长的意义范围内产生微小的变异,并将他的过程陷入亲密关系链中。选修课。过去的回忆,无论是物理的,时间的还是传记的,都是通过简洁地处理图像并因此转化为其他图像来重建的。就像记忆介入的每个动作一样,它是虚构的,因为它基于的不仅仅是您自己的记忆。
当然,在他的项目/变体中,有一个秩序,就像在混乱中一样,可以激发解释性意志,尽管也建议人们警告说,将其解散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也许它只是对它有用。作者。归根结底,在任何可能作为知识场所的档案馆,图书馆或展览馆中,产生的结果就是抽象的图像,就像音乐作品一样,允许某些组合系列的变化。
传记
哈里斯·埃帕米妮达(Haris Epaminonda)(1980年生于尼科西亚)是塞浦路斯摄影师,同时还是视频和多媒体艺术家,居住和工作在柏林。
Haris Epaminonda于2003年毕业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和金斯顿大学,并于2003年毕业。Epaminonda和她的搭档Daniel Gustav Cramer(生于1975年)从2007年开始从事他们的合作项目Infinite Library。场合数不胜数,包括2012年在利萨邦美术馆(Kunsthalle Lissabon)和卡塞尔dOCUMENTA(13)中。
Haris Epaminonda的作品融合了拼贴,装置,电影和摄影。最初,Epaminonda从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法国杂志和书籍中获取摄影图像。从2005年开始,她开始专注于黑白插图的人物和建筑拼贴。在2007年,她开始专注于彩色图像和纸张。 Epaminonda创建特有的图像成分,这些成分是通过拍摄发现的照相材料(例如在她的宝丽来系列(2008-09年)中)而创建的。 Epaminonda还使用Super8相机拍摄电影,然后将其数字化剪切-因此,这会创建不同长度的电影循环。
她的工作重点是广泛的拼贴画和多层装置,这些装置是图像,电影,照片,雕塑和发现的物体的结合。房间装置具有一定的方位,但也可以成为迷宫,将观看者置于特定的路径上。 Epaminonda被提名为2013年国家美术馆提名。
创造力
Epaminonda根据发现的对象创建叙事:照片,绘画,书籍,雕塑甚至建筑元素的各个页面。她总是以与她使用的原始资料不同的含义来构建叙述。他创作拼贴画,装置,美术书籍和录像艺术。她对搜索本身以及神秘化都很感兴趣。在他的作品中,他专注于交流的情感形式。通常,他通过给项目编号(卷)来为项目命名。因此,观众有更多的空间来解释它们,而且,他们的情感感觉比冷分析更为重要。对项目进行数字命名的原因也是它们相互渗透的事实。 Epaminonda的每件作品均源于上一部作品。
合作
Haris Epaminonda于2001年与Cramer会面。他们开始了合作,最终产生了Beehive,这是长期图书馆项目(无限图书馆)的基础。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艺术家根据自己选择的插图制作拼贴画/书籍。在找到的摄影镜头的基础上,为收集的照片和插图提供了新的背景,他们创建了50多个对象的集合。他们通过在展示它们的画廊中创建复杂的艺术装置来使用相同的做法。在建造展览时,它们不仅限于照片和插图,还可以创作专门的雕塑。
展览
展览Haris Epaminonda和The Infinite Library的补充文档
起初,这本书是躺着的。它只不过是其搁置表面略微升高而已,是一个谨慎的平台,高出桌子或桌子的表面。该书未经开封,表面几乎均匀,仅因其深色封面上的小瑕疵或擦伤而中断。他似乎不仅是封闭的,而且还是有点沉默寡言或专心致志,仿佛他不想太轻率地透露自己的秘密。它几乎不会在周围的白色平原上投射阴影。
一旦打开,这本书就构成了一个空间悖论。一方面,它继续向着二维的主题发展。它没有承认其完整的三维,而只是在其支撑上横向延伸。也许有一只手伸向他,以抚平起皱,难以折叠的页面。另一方面,可以说这本书在移动的方向开始增加。看不见或未读的页面像一连串可供探索的房间一样摆在我们面前。页码帮助我们记住前进的道路。在一页上-或最好在一页上,由于现代书籍始终是双联画-最好在一页上,眼睛将表面从一幅图像转移到另一幅图像(因为这是一本插图书籍),或者迷失在一张图片。行或文本块可水平引导您的视线,或强制其前后滑动以将视线垂直降低到页面底部。
我们使用的词汇表述(至少用英语)表明,这本书-这个奇特的物体永远不会完全本身-覆盖的空间量比起初看起来要大得多。我们谈论它几乎就像是一个可居住的空间。 “体积”一词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一组二维表面与我们从未真正体验过的厚度相关联,就像我们在每页的表面上一样被困住了。编辑谈论的是一本书的“长度”(即页数),在英语中,打印机使用“装订线”一词来描述两页文本之间的空白区域。这些隐喻与有限空间有关,并与一种包容有关。但实际上,这本书脱离了其边缘和边界,理论上是无限的。
无限图书馆中的物化空间和想象空间既适中又豪华,局部且不受限制。关于这些空间的惊人扩展-项目的不同片段似乎暗示着无限展开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无限图书馆》中看到对Jorge Luis Borges的故意致敬。阿根廷小说家在他的著名故事“通天塔图书馆”中,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它也是宇宙本身,一个光辉的空间,“由无限数量,也许是无限数量的六角形画廊组成,里面有巨大的通风井。中间,周围是非常低的栏杆。从任何六边形都可以看到上下两层:无尽。画廊的分布是不变的。”在这个严格地自我复制且没有止境的世界中,存在着无数的书籍,也就是说,所有可能存在的书籍都在图书馆中。假设故事的忧郁叙事者一定是在这无量的大量书籍中的某个地方,那本书是所有其他书籍的总和。
“通天塔图书馆”是博尔赫斯的故事中最明显的故事,可以说是无限图书馆所暗示的。双重的致命主题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不断出现。有时它作为实体或形而上学的对象与书直接相关。 “唐吉x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德(Pierre Menard,Don Quixote的作者)”一案引人注目,博尔赫斯(Borges)想象一位打算再次写出塞万提斯小说的作家:不要复制或模仿这本小说,而要像第一次写那样写与西班牙小说家。由此产生的书以一种新的(但同时又相同的)方式解开并重新排列了原始小说。文学史会自我折叠并吞下自己的尾巴:“梅纳德(也许是无意间)通过一种新技术丰富了超脱而原始的阅读艺术:故意的过时和错误的归因技术。这项技术充满了冒险中最平静的书本”。
理想的书-包含所有书的书-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作家和思想家最喜欢的幻想之一。例如,对18和19世纪的大百科全书进行动画处理。但是这种强烈的渴望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引起了特殊的共鸣。在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发行百科全书小说之前的几十年,象征主义诗人史蒂芬·玛尔玛(StéphaneMallarmé)梦见一本完美的书,模仿了现代报纸的开放性,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取代了相同(且“难以忍受”)文本列的一页又一页的单调乏味,该书将散布开来,使其边界不清楚。它会在繁华和离题的边缘处挣扎。文学将被明确地转换为页面上和页面外的图形布局问题。
毫无疑问,构成《无限图书馆》的物品,装置和电影都回荡着博尔赫斯和马拉默的小说。但是,Epaminonda和Cramer在这本书中所进行的转换和扩展-对其进行修改直到将其变成几乎虚构的嵌合体或杂合体库-与该书的解剖学在法国人提出的更为具体和平淡的术语上有更多共通之处小说家米歇尔·布托。在1964年首次发表的论文“作为对象的书”中-即在无限图书馆的许多书被创建的十年中-Butor分析了战后时期书的泛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是重新发现这本书是一个整体。不久之前,用于生产和分发它的手段迫使我们只谈论它的影子。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变化正在掩盖面纱。这本书开始以它的真实形式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
根据Butor的说法,传统书籍无非是一个“卷”或一个容器,内容谨慎而统一。叙述或常规文章必须从头到尾,从左到右阅读:“该卷的其他两个维度和方向-如果是专栏,则是从上到下;从页面上的更近到更远-它们通常被视为完全在第一轴之后”。这些方向或次要维度构成了Butor现代书中自由和自由的空间。他首先要记住的是我们没有按顺序阅读的那些书,例如目录,词典和手册。我们可以在列表中添加各种插图文字:百科全书,艺术专着,技术论文和有关自然历史或偏远和异国地方的书籍。
按照Butor的计划,这些书是无限制的,是由网络或模式组成的,不是直线的叙述线或清晰定义的段落和章节。换句话说,这本书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或者换句话说,在当代插图书中,我们再次发现了该书作为对象的原始无限性。 Butor提醒我们,最早的现代书籍装饰有脚注,光泽和指向体积空间之外的资源。 Butor认为,正是本书不断发展的趋势使我们现在必须恢复;简而言之,这本书的无限性又意味着图书馆或档案馆的无限性质。
无限图书馆的书不再是他们自己。它们显然具有相同且受限制的对象的外观;它们的特点是外部设计特别节俭:深色封面,无防尘套,清洁的防护罩和谨慎的色标,其中包含艺术家的姓名和每本书在该系列中所占的位置。在现实中,看似统一且完整的书卷已被切角并打开,内翻并通过从任何地方取下的阴险插件来恢复。这本书不再局限于暗示其外部的参考文献,而是最终将其外部结构集成到其自身的结构中。同时,这种感觉占据了上风,那就是书本本身就折叠起来了—在缺乏逻辑结论的运动中,书本存在的各个维度之间产生了混乱。
通过拆解书籍并将其重新配置为书目怪兽,Epaminonda和Cramer对与之合作的对象执行了几种不同的操作。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一本书的图像插入另一本书的页面中,使第一卷看起来基本上是完整的。在某些情况下,插值几乎不会引起注意,只是用一个插图替换另一个插图,以使页面的图形节奏不会中断。在其他情况下,插入物是在容纳它们的现有页面,入侵者或未掩盖的寄生虫之间滑动的新纸张。有时,杂乱的颜色渗透到文本和图像的单色分布中,并进入页面所调用的概念空间。
但是,有些酌处权占上风。无限图书馆并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蒙太奇练习。即使在视觉上差异最大的情况下,所涉及的书似乎也尊重彼此的设计和生产惯例。他们的联合微妙而讽刺,几乎是中立的。但是,即使不是现代主义并置的暴力,也有一些暴力处于危险之中。这是Butor对另一文本内的图形表示所评论的内容:“在另一页面内复制一页甚至一行会生成光学分区,其属性与引用的常规分区完全不同。它在文本中引入了新的张力,就像我们今天在城市中经常被口号,标题和标志所覆盖的那种张力一样,被歌曲的噪音和中继的单词,震撼和震撼所侵袭。当我们阅读或听到的声音被残酷地隐藏时,它们就会产生”。无限库将图像视为被替换的引号:它们引用中断页面之外的元素,并在页面本身的平面中引入新的区别或距离。
有时,该页面会在“无限图书馆”中保持原样,而不会从另一本书上获取任何图像。作为交换,各种几何图形被神秘地添加到页面中。图案可能非常微妙,不会改变图像或页面,就像在小圆圈中随机点缀着8号书(1956年的Im Wald und auf der Heide,或1956年的Im Wald und auf der Heide)中的野生动物照片一样,或者,但不会隐藏运动员。 9,德意志体育馆,于1967年出版。在其他情况下-1951年的Praxis der Farben-fotografie,这是第11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干预更为极端:在其中,每张照片几乎都被完全隐藏起来。一个平滑的黑色矩形,仅留下可见的,本质上是抽象颜色的狭窄边框。尽管如此,其效果部分是暗示一个新的空间-类似于Butor的“亲密感”-在读者的眼睛和平面之间打开。
本书11的案子在另一种意义上是说明性的。 Butor指出的这本书的特性之一是其固有的对称性。由于其物理形式和图形设计,该书已经开始复制:“在这方面,现代西方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将其表现为双联画:我们总是一次看到两页,一张面对另一个在活字帖中央部分的并集会创建一个可见度降低的区域,因此光泽通常对称分布:右页边距最适合右页,左页边距最适合“ 7”。在“无限图书馆”中,有时同一本书的两个副本被巧妙地散布,在此各处的页面意外地重复。最雄心勃勃的案例是第12号书,即《史威根德·韦尔特》(Die Schweigende Welt,1956年):整本书已被复制以形成一个对称的整体,其中水下探险的照相序列作为照相浪潮或作为一次旅行的例子而前进和后退。时间。
由Epaminonda和Cramer修改插图的书籍主要追溯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也许并非偶然。正如Butor在1960年代初期所指出的,战后书籍设计和生产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彩色摄影的使用和多种设计的使用,包括血腥图像的使用-引起了书籍概念的扩展概念。可以在页面的同一抽象空间中呈现不同类型的视觉和文本内容的功能。 Butor认为,“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将迫使书籍变得越来越’精美’,越来越密集。我们将从术语这个琐碎的意义上的消费对象变成研究和沉思的对象,它转变了我们认识和居住宇宙的方式”。
这本书几乎是乌托邦式的计划,对Butor来说,既是当代信息技术的效果的结果,也是必要的平衡。在录制声音的时代,技术使动态图像和计算机化数据存储的开始成为可能,使这本书成为同时和全面知识的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无限图书馆还是信息和人工制品的现代主义风格的考古学。每本书本身都是一个神秘的对象,也是构成博物馆或项目概念档案的最广泛的关系和提醒网络中的一个片段。
Epaminonda和Cramer对该项目的称谓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所有库至少在原则上都是无限的。实验作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空间的种种》中,反思了我们可能称之为页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即页面最初只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变成某种东西的方式,即使只有少数迹象引导着读者水平和垂直。像Butor一样,Perec认为这些页面可能无限扩展:“如果我们对国家图书馆中保存的所有印刷作品进行剥皮,并仔细地将它们的页面彼此紧紧地延伸,我们将完全覆盖圣埃琳娜岛或特拉西梅诺湖” 9。他写道:“几乎所有的东西,一次或一次都经过一张纸”:信件,报纸,正式文本,购物清单,火车票和医生收据不知疲倦地记录着整个宇宙。庞大的图书馆显示了每个人类生活的踪迹,并反映了“真实”图书馆的扩展。
但是,文本和图像的这种泛滥不应该仅仅以其扩展能力或递归和内部重复为特征。这些晚期的现代主义作家在书中和图书馆中都有一种物化的希望-即使他们乐于将书作为对象进行剖析,并将图书馆作为所有人类知识的典范加以剖析,即使他们承认这一点(如博尔赫斯写)图书馆是无限的和周期性的,而且一本书还不那么复杂和难以理解-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放弃。这是乐观主义,优雅地表达在同一时期的书和档案中。
在阿兰·雷斯奈斯(Alain Resnais)的诗词纪录片《世界的一切记忆》(1956年)中,巴黎国家图书馆不仅体现了人类知识的总和,而且体现了发现和解放的集体计划:“这里预示着一个时刻,会解决所有难题,而此时这个宇宙和其他宇宙将揭开它们的钥匙。这是因为读者坐在一堆普世知识的前面,会一次又一次地找到相同的秘密,这些秘密回应着一个美丽的名字:幸福”。无限图书馆在对想象中的档案进行暗示性和神秘性重组时,容纳了这个乌托邦计划的幽灵,即使它在博尔赫斯之后向我们保证,这个秘密无休止地被重复而且永远不会被揭露。
安达卢西亚当代艺术中心
安达卢斯当代艺术中心(CAAC)成立于1990年2月,旨在为当地社区提供一个研究,保存和促进当代艺术的机构。后来,中心开始在其永久性当代艺术收藏中获得第一批作品。
1997年,Cartuja修道院成为该中心的总部,此举对该机构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CAAC是一个依靠安达卢西亚政府(Junta deAndalucía)组成的自治组织,接管了前Conjunto Monumental de la Cartuja(Cartuja纪念碑中心)和塞维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塞维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
从一开始,该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制定一项活动计划,试图从各个方面促进对当代国际艺术创作的研究。临时展览,研讨会,讲习班,音乐会,会议,独奏会,电影周期和讲座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交流工具。
该中心的文化活动计划辅以参观修道院本身,该修道院是我们悠久历史的产物,是我们艺术和考古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