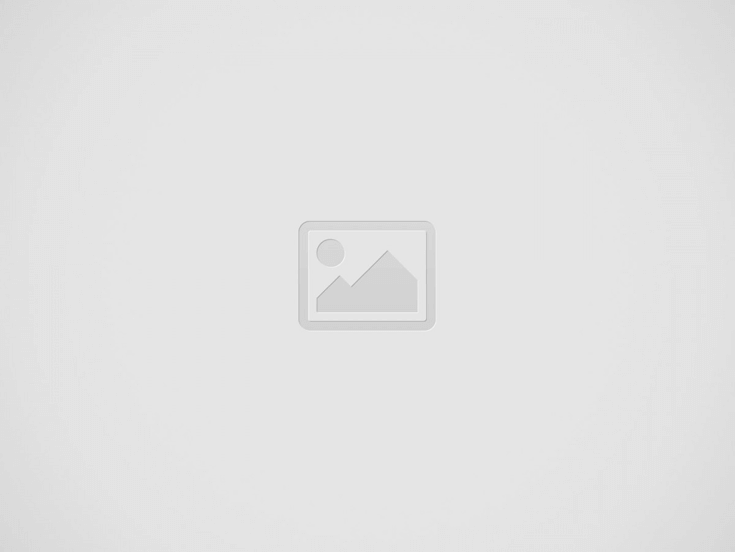

柏林爱乐乐团是德国柏林的音乐厅,也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所在地。
爱乐厅位于城市蒂尔加滕(Tiergarten)的南边缘,就在前柏林墙的西边。爱乐乐团位于赫伯特·冯·卡拉扬·斯特拉塞大街上,以乐团服役时间最长的首席指挥而得名。该建筑是波茨坦广场附近文化机构Kulturforum建筑群的一部分。
爱乐乐团由两个场馆组成,大礼堂(GroßerSaal)有2440个座位,室内音乐厅(Kammermusiksaal)有1180个座位。尽管是一起构思的,但较小的大厅却在1980年代开幕,距主楼仅20年。
历史
汉斯·沙鲁恩(Hans Scharoun)设计了这座建筑,该建筑建于1960年至1963年。它于1963年10月15日开幕,赫伯特·冯·卡拉扬指挥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它的建造是为了取代旧的爱乐乐团,该乐团于1944年1月30日,即希特勒就任总理十一周年之际被英国轰炸机摧毁。该音乐厅是一栋不对称且类似帐篷的单一建筑,主音乐厅为五边形。一排排座位的高度随距舞台的距离不规则地增加。舞台在大厅的中央,四周都是座位。这座建筑开创了所谓的葡萄园式座位安排(露台围绕中央管弦乐队的平台上升),并成为其他音乐厅的典范,包括悉尼歌剧院(1973年),丹佛
爵士钢琴家戴夫·布鲁贝克(Dave Brubeck)和他的四重奏在大厅录制了三场现场表演。戴夫·布鲁贝克(Dave Brubeck)在柏林(1964),在柏林爱乐乐团(1970)演唱,而我们又一次在一起(1973)。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1969年在大厅里的现场表演也已通过DVD发行。
2008年5月20日,大厅发生火灾。消防员切开开口以到达屋顶下方的火焰时,屋顶的四分之一遭受了相当大的破坏。大厅内部遭受了水的破坏,但在其他方面“总体上未受到损害”。消防员使用泡沫限制了伤害。起火的原因是焊接工作,没有对建筑物的结构或内部造成严重损坏。表演如期于2008年6月1日恢复,旧金山交响乐团青年管弦乐队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伯恩伯格大街上的旧爱乐乐团
成立于1882年春天的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场音乐会在夏洛滕堡花园餐厅“ Flora”举行。该乐团的第一个永久性住所是1882年夏天,由古斯塔夫·诺布卢赫(Gustav Knoblauch)在克罗伊茨贝格的伯尔尼大街22a / 23号为卢多维科·萨塞尔多丁1876年的前溜冰场建造。1888年,爱乐乐团的指挥官弗朗兹·海因里希·施瓦希滕(Franz Heinrich Schwechten)的建筑被重新修建,这是一个没有桌子的Bestuhlten音乐厅。“但是,在矩形房间中,灰泥得到了帮助,并烫了一些东西,”其出色的声学效果受到赞誉。1898年,大厅开始变小,施维滕在下层院子(科特纳路32号)制作的爱乐乐团的天窗大厅和贝多芬大厅建筑,以保留其他空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过渡期
战后年代,柏林爱乐乐团最初使用各种替代场所:音乐会通常在泰坦尼亚宫举行,音乐会的录音经常在达勒姆的耶稣基督教堂进行。
投标
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建筑招标于1956年由柏林州进行,邀请了14位建筑师参加。最初的位置应最初是在联邦军事学院(Jonesmsthalsche Gymnasium)毗邻的联邦议院(Bundesallee)上的一块地块。1957年1月,汉斯·沙鲁恩(Hans Scharoun)的设计获得了第一名。在爱乐比赛中,沙罗恩扬言要重蹈覆辙,这在卡塞尔歌剧院的新建筑中得到了体现。尽管沙罗恩在那里获得了第一名,但他的计划在最初遇到困难后并未实施,而是委托了另一位建筑师。
尽管经过16个小时的协商,陪审团将夏洛恩的爱乐乐曲奖授予了第一名,但该决定还是以9票对4票做出的,因此没有四分之三的多数票。只有在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和上诉人汉辛兹·斯塔克·施密特(Hansheinz Stuck Schmidt)(陪审团成员之一)介入之后,沙罗恩才最终受命起草约束力。
新地点
但是,应该再次推迟施工的开始时间:在公开讨论中,目标位置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与旧的爱乐乐团相距太远。最终,在1959年,柏林众议院决定将新建筑搬迁到现在的位置。
作为柏林转变为“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的一部分,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计划建造一个巨大的士兵大厅,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德国士兵。因此,地点的选择也标志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巨大狂潮。紧挨该物业的还有国家社会主义行动T4的行政大楼。该建筑物在1944年被炸弹炸毁,严重破坏,随后被拆除。今天,在爱乐音乐厅旁竖立了一个纪念馆,该纪念馆的扩建于2014年9月开始。
新的爱乐乐团最终成为战后计划中的文化论坛的第一座建筑。它是由Hans Scharoun设计的,历时37个月(奠基石铺设:1960年9月15日,封顶仪式:1961年12月1日,开业:1963年10月15日)建造。建筑成本总计约1,700万马克(今天的购买力调整后约为3,700万欧元)。
开场
最初的落成典礼计划于1964年春季进行,但后来(针对建筑工地的考虑)提出来,以允许秋季定期时段的开始。在新的爱乐乐团开幕式上的演讲让建筑评论家阿道夫·阿恩特(Adolf Arndt)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幕音乐会(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构成了1963年柏林非斯沃申的结局。
建筑
当爱乐乐团于1963年开业时,它仍然位于西柏林的外围,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它成为新城市中心的一部分。它不寻常的帐篷状形状和鲜明的鲜黄色使它成为城市的地标之一。其不寻常的建筑风格和创新的音乐厅设计最初引起了争议,但现在已成为全世界音乐厅的典范。
地点
该建筑今天与室内音乐厅,柏林乐器博物馆以及其他在波茨坦广场不远的柏林文化公园同属于建筑物,并且紧邻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新国家美术馆和波茨坦广场。也是在夏洛恩计划建造柏林国家博物馆的波茨坦大街之家之后。
Potsdamer Platz最初的结构状况是由于建筑物的方向,今天可以将其视为“回旋处”(主要入口朝Tiergarten方向,然后回到Potsdamer Platz)。在建造时,该地区是休憩区,直接在休耕的波茨坦广场上的部门边界上,在爱乐乐团的建造过程中,柏林墙就是在此建造的。只有在团聚后的柏林波茨坦广场才获得其当前的发展,并因此获得其最初的交通意义。但是,也可以通过爱乐音乐厅和室内音乐厅之间的连接通道从停车场一侧进入两座建筑物。由2009年这个“后门”的醒目设计(附加新徽标,
外观设计
由于其特殊的,类似马戏团的设计以及在爱乐乐团中部的音乐会领奖台,建成后不久就被戏称为“马戏团卡拉扬尼”,指的是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见马戏团萨拉萨尼)。这个名字应该来自柏林的地方。另一个绰号是“音乐会盒”,它的金黄色镶边和形状让人联想到两个礼盒的巧克力盒。
在1984年至1987年之间,除了根据汉斯·沙鲁恩(Hans Scharoun)的原始计划而设计的爱乐乐团之外,室内音乐厅也是根据埃德加·维斯涅夫斯基(Edgar Wisniewski)的计划建造的。两座建筑物都已连接。
随着第二栋建筑的增加以及爱乐乐团对蒂尔加滕(Tiergarten)的定位,这座建筑的许多细节在作为访客进入综合大楼时不再立即显现出来。在从开放时间开始的航拍照片上,许多细节从一开始就更容易识别。其中包括沙罗恩(Scharoun)著名的航海设计元素,例如“舷窗”,以及将建筑划分为水平的白色基础,容纳了门厅和行政翼,以及高耸的金色(当时为米色)。音乐厅。在建筑物的北侧和西侧,外面有一个类似露台的画廊,可以在公共休息时间开放,也可以从那里进入花园。
“金色”外墙立面
在开幕式上,爱乐乐团还没有“金色外皮”,因为它掩盖了今天的外墙。尽管沙鲁恩已计划了外墙立面,但出于成本原因,最初并未实施,混凝土外墙仅使用了临时的cher石色油漆。选择o色作为对勃兰登堡城堡和豪宅传统颜色的参考。
仅仅几年后,爱乐乐团的Umschalung受到了湿气的损害,伪装的主题再次被接受。仅在1979年至1981年间,在对立的州立图书馆建成后,柏林参议院才最终将阳极氧化的铝板追溯性地贴上了-(几乎)装饰着Staatsbibliothek高级杂志的那些(见下文)。
但是,毫无疑问,金版并不是沙朗的初衷:他曾计划过带有三维图案的方形“彩版”。烟囱白板南侧的附件符合此最初计划的伪装,因为它们仍然可以识别较晚的图纸,但是后期建造阶段的原型甚至配备了小的粉红色和灰色区域。
同时,在爱乐乐团的外墙翻新过程中实现了细节,由于成本原因,在对面的Staatsbibliothek的高级杂志的金色镶板中省略了该细节:单个金阳极氧化铝板配有半透明聚酯纤维头巾。沙鲁恩在州立图书馆的展台上承诺了与铝板的金字塔结构相关的微妙照明效果。如今,人们发现这种想法在实践中仅能适度发挥作用:与1984年建造的室内音乐厅相比,爱乐厅的外表看起来暗淡而肮脏-只有乍一看,才可以意识到这不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所致。盘子(无论如何相差仅三年左右):室内音乐厅的金色盘子上没有半透明的盖子。
在爱乐大厅的西侧,靠近紧急楼梯,您可以看到所有三种外部覆层:在上述的烟囱中,白色的塑料面板与最初的设计大致相对应;在它的左侧,铝板覆盖有聚酯板,在其右侧(楼梯本身)上是无盖的阳极氧化金板。
室内设计
音乐厅
爱乐音乐厅提供2250个座位[供比较:后来建造的室内音乐厅可容纳1180名观众。
大厅的结构是不对称且类似帐篷的,其设计基于三个互锁的五边形的原理,至今仍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标志。但是,这种不对称性在房间的平面图中非常巧妙地实现,并且具体通过大厅中的细节来实现:除其他事项落在左侧区域外,观众区很远,其中设有两个工作室。另一侧是风琴(见下文),后面是一个空的控制室,该室可配备带有演播室设备的外部设备。
由于不规则的登机平台,座椅从各个侧面都可以看到几乎居中放置的舞台。通过这种特殊的安排,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分离被大大消除了。从相应的席位,观众z。由于表演中的指挥者面朝表情,因此,在声音平衡方面较差的地方(例如,紧靠打击乐(H区))具有自己的品质。许多艺术家喜欢在爱乐乐团的表演中坐在观众中间。这些可以依次从各个角度观察演员,具体取决于座位。然而,
沙鲁恩本人将访客区的布置描述为“上升的葡萄园”。梯田的梯田打破了观众通常的连贯结构:每个街区将大约75-100个席位组合在一起,使它们在社会层面上“亲密”,但在听觉和身体上却是连贯的。倾斜和布置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使观众在舞台视野中尽可能少地互相阻碍。
乐团一直将中央音乐厅与传统音乐厅区分开来,这一直被批评家认为是对音乐会演出社会结构的重新定义。例如,在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之际,柏林日报写道:“爱乐乐团更开放的空间可以实现所有音乐的传播是不正确的,而在音乐厅则成为资产阶级仪式的一部分,在Prokofiev之前,似乎一直监视着附着在Bach石膏头上的物体?”
舞台的位置和独特的梯形结构后来成为许多新音乐厅建筑的模型(见下文)。1956年,斯图加特·利德哈尔(Stuttgart Liederhalle)开幕的莫扎特音乐厅中已经存在类似的露台结构,适合游客使用。
室内乐厅
室内乐音乐厅从成立之初就被计划作为爱乐乐团的一部分,但直到汉斯沙鲁恩去世15年后才于1987年开放。他留下了草图,他的搭档埃德加·维斯涅夫斯基(Edgar Wisniewski)从该草图中得出了该结构的概念。Scharoun的素描中已经指定了室内乐厅的六边形形状,Wisniewski在他的设计中采用了六边形形状。洛萨·克雷默(Lothar Cremer)再次担任建筑师的声学顾问,而座椅的放置和分组受他的分析影响很大。
像大礼堂一样,室内乐厅的概念也源于音乐家的平台。音乐会平台内置了许多不同的可能性。例如,可以将其降低以形成半阶段演出的管弦乐队。平台的灵活性是建筑师的重要关切,他寻求为当代音乐表演创造合适的空间。
所谓的“动作环”穿过座位区的一半。它使音乐家可以从其他位置演奏。
大厅外围的画廊通过音乐家的可变放置而类似地允许附加的空间效果。
为了与门厅明亮,明亮的中央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维斯涅夫斯基选择了深色,暗淡的外部色彩,这与大,小音乐的二元性相对应。在室内乐厅楼梯设计的免费,类似桥梁的元素中,维斯涅夫斯基再次使用了主礼堂中的元素。
Wisniewski继承了Philharmonie的许多设计功能,例如彩色玻璃窗,并将其整合到室内乐厅。彩色玻璃墙的灵感来自云层和天空。柏林爱乐基金会(Stiftung Berliner Philharmoniker)的室内音乐会的介绍性演讲在这里举行。门厅还用于展览。
主礼堂
“音乐在即兴创作的地方,人们会立即围成一个圆圈,这是偶然吗?”出于这种考虑,汉斯·沙鲁恩(Hans Scharoun)开发了这个音乐厅。与传统的音乐家和听众彼此相对的传统布置不同,在沙鲁恩(Scharoun)的概念中,重点放在平台上,以音乐家为中心,听众围绕该平台分组。
爱乐厅的主要礼堂以其出色的音响效果和建筑而闻名。在计划中,沙罗恩与柏林的声学家洛萨·克雷默(Lothar Cremer)密切合作
技术大学。许多建筑细节(例如,台阶和栏杆的陡度和高度)都是通过声学确定的。尽管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以后仍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1975年提高音乐会平台以增强琴弦的声音。
“大厅被认为是山谷,管弦乐队坐在床上,周围是上升的梯田葡萄园。” Scharoun将平缓倾斜的梯田形象转化为他为2218位与会者设计的座位区。建筑师的愿景是为民主社会创建一个音乐厅:不会密封各个层级,并且所有座位均具有统一的声学品质。
与将管风琴直接放在乐团平台上方的传统音乐厅不同,沙鲁恩将乐器移到房间的右边缘。该风琴有72个寄存器,四个手册和踏板,可以通过跟踪器(机械式)或移动式电动控制台进行演奏。它来自卡尔·舒克(Karl Schuke)的柏林管风琴工作室。
这些大理石面百叶窗的后面隐藏着合唱风琴的烟斗。它的十二个停靠点分布在两个手册和踏板上,就像大型风琴的手册和踏板一样,它们是通过移动式电动控制台演奏的。合唱管风琴也是由卡尔·舒克(Karl Schuke)的工作室建造的。
礼堂墙面的选择也是基于Cremer和Scharoun的声学判断。带有细孔的坎巴拉木材的壁固定在吸收性背衬上,以消除平台一部分的回声效应。
作为观众水平的“葡萄园景观”的对应物,沙鲁恩创建了一个天花板,他将其称为“天空景观”。许多小灯的目的是唤起“星空穹苍”的联想。顺便说一句:天花板的高度是根据每个座椅10 m3空气空间的声学要求确定的。
天花板的形状让人想起带有三个凸拱形拱门的帐篷,可确保声音的均匀扩散。在乐团的平台上悬挂着“云朵”-弯曲的聚酯表面充当反射器,使音乐家能够更好地相互聆听。
工作室
柏林爱乐乐团的数字音乐厅视频将古典音乐音乐会流式传输到平板电脑,智能手机,smartTV或PC。声音质量类似于CD,声音质量类似于HD电视。这样,数字音乐厅几乎完整记录了柏林爱乐乐团及其音乐合作伙伴的艺术作品-从首席指挥西蒙·拉特爵士到著名的客座指挥和独奏家。
票房
从这张票房可以买到由柏林爱乐基金会(Stiftung Berliner Philharmoniker)发起的音乐会的门票。
门厅
与传统布局相反,门厅位于音乐厅的右侧(正门有点像“位于建筑物的一角”)。由于音乐厅的礼堂座位呈阶梯状错开,门厅以“迷宫式树枝”形式的楼梯为主。这两种情况刺激了直观的方向,有时访客很难找到正确的访问点(总共有27个)。作为指导,可以在如今用来建造酒吧的门厅的背面使用四个倾斜的支柱:这些支柱支撑着礼堂的上方C块,并准确标记了大厅左右两侧之间的中心轴。窗户正前方是亚历山大·卡玛洛(Alexander Camaro)的玻璃砖元素(见下文),
自1963年以来,柏林爱乐乐团一直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故乡。不仅如此:许多其他推广者还使用爱乐乐团的主礼堂和室内音乐厅进行音乐会和其他表演。文化的融合和艺术的交汇之地–正是建筑师Hans Scharoun在构思这座建筑时所想到的。让我们开始探索爱乐乐团,其建筑和历史。
大约十年后,沙罗恩(Scharoun)在对面的柏林建筑博物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使用了内部设计细节的特定设计,例如栏杆,地板和窗户(另请参见“建筑艺术”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不仅由简洁的金色立面立面,也揭示了与两栋建筑的室内设计的直接关系。
楼梯和窗户
这样,就可以到达右侧的座位区,赫尔曼·沃尔夫·霍尔(Hermann Wolff Hall)和南厅,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前的活动在此举行。亚历山大·卡玛洛(Alexander Camaro)的彩色玻璃墙-这里是绿色和蓝色的阴影-与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种彩色灯光效果,沙鲁恩(Scharoun)试图增强建筑物的节日特色。
楼梯用作连接各个楼层的桥梁。他们为休息室的空间增添了浮动的光彩,这也受到海军建筑的启发。
玻璃组成:亚历山大·卡玛洛(Alexander Camaro)的彩色玻璃墙-这里是灰色和粉红色的阴影-与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种彩色灯光效果,沙鲁恩(Scharoun)试图增强建筑物的节日特色。
灯由GünterSsymmank设计。每个表面都由72个五角形聚酰胺表面组成,这些表面附着在球形塑料框架上。
小型楼梯(其中一些在设计上像桥一样)通向礼堂门,礼堂门也起着声音缓冲的作用。
南大厅,指挥家胸围
与主休息室宽敞的开放性(包括上北画廊休息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鲁恩(Scharoun)将南休息室设计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引起沉思的撤退。Stiftung Berliner Philharmoniker主要礼堂音乐会的介绍性演讲在这里举行。
他是柏林爱乐乐团Orchester的第一位伟大的管弦乐教练:Hans vonBülow(1830-1894)。在乐团的经纪人赫尔曼·沃尔夫(Hermann Wolff)的倡导下,随着乐团与早期几位杰出指挥的合作,他于1887年成为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布洛(Bülow)设定了高标准,并进行了不懈的排练。柏林爱乐乐团在指挥棒的指挥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出生于匈牙利的亚瑟·尼基施(Arthur Nikisch,1855–1922年)从1895年开始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直到1922年去世。他以管弦乐小提琴家的职业生涯起家,无与伦比的诀窍,以其魅力,感召力和他凭直觉的诠释艺术。在尼基施的领导下,柏林爱乐乐团制作了第一张唱片。
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Furtwängler,1886年至1954年)于1922年接替亚瑟·尼基施(Arthur Nikisch)担任柏林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与他的前任不同,他立即成为当代曲目的冠军,在希特勒掌权后,纳粹不满。尽管富特文格勒从未参加过该党并认为自己是非政治人物,但该政权仍对富特文格勒表示崇高的敬意。1945年,他被盟军禁止指挥,但在1947年的法庭上,他被纳粹化,因此能够再次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但是直到1952年,他才正式被恢复为乐团的首席指挥,直到两年后他去世为止。
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Furtwängler)逝世后,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年至1989年)成为乐团的首席指挥-近35年。在他的指导下,它发展出特定的声音和出色的完美音质,并因此闻名世界。爱乐乐团与卡拉扬(Karajan)于1963年一起搬入了夏洛恩(Scharoun)建造的爱乐乐团。乐团与他一起成为媒体明星。指挥家还要感谢另外两个机构:卡拉扬(1967年)创建的萨尔茨堡复活节节和管弦乐学院。
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年)从1990年至2002年担任首席指挥。他努力争取比他的前任更透明的管弦乐声音。首席指挥在演唱会节目中强调了自己的重点。阿巴多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大型音乐会以特定主题为主题,例如普罗米修斯,浮士德或莎士比亚,以及与古斯塔夫·马勒的合作。
通道门厅
通道门厅将爱乐乐团与室内乐厅相连。
贝尔奥利兹的“交响曲幻想曲”和穆索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的表演为钟声。爱乐打击乐家弗雷迪·穆勒(FrediMüller)提出了一种可以在中间支撑而不是挂起来的铃铛的想法,因此更适合在乐团中使用。它们是由位于黑尔布隆的Bachert钟形铸造厂在柏林爱乐乐团的友人协会(Gesellschaft der Freunde)的财政支持下制造的。
建筑艺术
门厅地板由Erich Fritz Reuter(1911-1997)设计。
西北侧的彩色玻璃窗由亚历山大·卡玛洛(Alexander Camaro)(1901-1992)设计。
门厅中著名的“爱乐灯I”由GünterSsymmank(1919-2009)设计。
花园设计由Hermann Mattern(1902-1971)接管。
提到的所有四位艺术家还参加了对面的柏林州立图书馆的设计,该图书馆是由沙鲁恩在几年后设计的。
屋顶的雕塑(“凤凰”)与音乐厅本身一样,面向德国国会大厦,由雕塑家汉斯·乌尔曼(Hans Uhlmann)设计。
Bernhard Heiliger(1915-1995)在大厅设计了雕塑。海利格后来又为国家图书馆制作了两部作品。
大厅和舞台后面房间的家具由Piter G. Zech设计。
在爱乐音乐厅和Tiergartenstraße之间有一个小的绿色区域,1959年在此竖立了Orpheus雕塑。她来自Gerhard Marcks的工作坊。
正门正上方是不锈钢制成的简单字母,上面是建筑物的象征,是多层嵌套的五边形。Fittkau Metallbau和Kunstschmiede公司于2010年更新了脚本和符号。
声学
管弦乐队在观众中间的独特定位,使爱乐乐团对声学设计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偶尔有传言说大厅原本的声学效果很差,然后仅需逐渐将其提高到可接受的水平,这是不正确的。
促成这种说法的事实可能是,出于成本原因,在最初计划的精心设计的讲台上省略了结构,这最初导致各个乐器组的可听性出现孤立的问题。经过各种临时解决方案后,最终的改进仅在开业后的十年内进行了(见下文)。新大楼的强烈宣传也使有时尖锐和夸张的批评在辩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后来沃尔夫冈·斯特雷斯曼(Wolfgang Stresemann)将爱乐乐团的最初音响效果描述为“非常,非常糟糕-十分糟糕”。
相反,大厅从一开始就经过精心设计,以汉斯·沙鲁恩(Hans Scharoun)的精神为基础,他从内而外地规划了他的建筑。声学上的考虑也是平面和屋顶形状中非常规外观的结果。
在规划比赛时,沙罗恩已经在最早的最佳计划阶段就开始工作了,他在参赛作品的设计中与来自柏林工业大学的洛萨·克雷默(Lothar Cremer)紧密合作,作为顾问,他认为领奖台的位置概念是最佳的在建造期间和建造期间,模型也以1:9的比例使用:电脉冲产生爆破脉冲以记录回声图。(这里的研究目标不是设置混响时间,而是检测和校正颤动回声。)
对于室内声学,尤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房间的“声音”:混响的时间和特征,房间的共鸣,颤动的回声等。
音乐会观众的声音图像的平衡:房间中声音的分布,乐器的可听性
讲台/舞台上的声音平衡:音乐家之间的可听性
房间的“声音”
对于交响乐团在音乐厅的混响时间,中频(房屋完全被占用)的大约2秒的值被认为是最佳的,较短的时间被认为是“糊状的”(客厅的气氛),较长的时间使声音变淡。声音很快(因此,例如,不再认为大型教堂中的交响乐团令人愉悦)。在爱乐乐团中也可以达到这一价值。
但是,与外行人的假设不同,在新建筑物中设置混响时间不会带来很大的声学挑战,因为它主要由所需的空间大小(爱乐乐团为每人10立方米)计算得出。表面材料可能会受到影响。
为了使测试情况(无观众)和音乐会情况(有座位的座位)之间的声学差异尽可能小,例如,座位的底侧装有吸音垫。在无人房间中,混响时间与有人椅子时相似。
由于其不对称的布局和缺乏平行的表面,大厅为避免经典问题(例如回声和驻波(房间共振))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大厅的天花板上装有136个棱形的亥姆霍兹共鸣器,该共鸣器装有吸音材料,还可以通过调节间隙开口进行调谐。由于它们的形状,它们同时充当扩散器,因此还提供了所谓的“早期反射”(直接反射和可定位反射)的分散。通过这些措施,爱乐乐团实现了其特殊的混响特性,其特点是早期反射少,扩散混响比例更高,因此与传统的矩形大厅相反。B.
音乐会观众的声像平衡
o。G.房间声音的特征还导致主要声源(即单个乐器)的出色定位性和音色的选择性。房间中声音的均匀分布很大程度上是由多凸天花板完成的。这是基于洛萨·克雷默(Lothar Cremer)的想法:沙鲁恩最初提供的是圆顶状结构。
然而,一开始批评的主要点恰恰是管弦乐声音平衡的这一方面,尤其是弦乐通常听不到足够大的声音。其原因很快被确认为讲台在大厅中的位置过低。当时的导演沃尔夫冈·斯特雷斯曼(Wolfgang Stresemann)在谈到夏洛恩对大厅的描述时说:“夏洛恩的触底声显然太深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计划了更高的讲台,但由于成本原因并未实现。讲台高度的提高应持续十多年:
1964年夏天,首先增加了整个领奖台,带来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没有使Karajans完全满意。
1973年,出于审美原因,在电视录制中安装了半圆形阶梯式讲台,这抬高了乐团的后部。尽管这只是临时的,但卡拉扬从那时起在他的表演中一直使用它,因为他深信声音的效果,使单个音乐家的听觉更好。使用该应用程序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其他音乐会的结构将被各自删除,这意味着需要使用专家。出于安全原因,必须在一年后停止使用基座。
最终,在1975年夏天,以埃德加·维斯涅夫斯基(Edgar Wisniewski)的设计为基础,以目前的形式安装了讲台。半圆形台阶形状可以整体和部分进行机械调节,并且可以适应不同的音乐会情况。
但是,物理情况不能通过结构性声学措施来改变:当然,靠近乐团的舞台一侧和后面的舞台上的主观声音是不平衡的。首先,在这里,比起更远的距离或在经典的块(AC)中,特别接近的乐器组更加突出,因为在这里,相对振幅差只是更大。在这些地方,另外的问题是由于仪器的方向性,即z。B.对黄铜有很强的影响力,并且在独奏唱歌方面表现最佳。负责的声学家洛萨·克雷默(Lothar Cremer)说:“因此,独奏歌手音乐会将始终是爱乐乐团的大胆尝试,”他认为合唱团认为没有任何困难。
音乐家之间的听觉
与许多游客的假设相反,悬挂在舞台上方的凸出声音元素并不是主要为观众安装的,而是为音乐家安装的:在讲台上方22米的天花板高度处,这些由玻璃纤维制成的反射器缩短了观众的声音路径。早期的思考,从而保证了乐器演奏者之间的可听度。但是,反射器还在靠近舞台的舞台上,尤其是在中层,在声学上提供令人愉悦的临时反射。这些元件通常也被称为“云”,其高度和倾斜度易于调节。最初,沙鲁恩计划了一个大型反射器,但是后来又分成了十个。应Scharoun的要求,出于审美原因,与Cremer的设计相比,它们的尺寸有所减小,在开幕时,这些较小的反射器悬挂在大厅的天花板上。但是,在第一场比赛休息时,就已经将它们换成了更大的反射镜,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们。
直播技术
该建筑符合“技术前卫主义”的建筑和音乐传统,因为该建筑本身和乐团领导人(尤其是赫伯特·冯·卡拉扬)都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爱乐乐团的内部声音和广播技术自然可以在几年内在没有太多可见干预的情况下,以高画质和声音质量将整个音乐会作为视频直播和互联网上的存档材料进行分发。迄今为止,柏林爱乐乐团是唯一拥有这种官方机构的音乐厅(自2008年11月由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主持)。